
莆田母親河木蘭溪
仇春霞
每一條匯入大海的河流都曾無限拉升過一些孩子懵懂的夢想,即使是生於貧窮,也無法限制他們對遠方的想像。
蔡襄生在莆田。木蘭溪是母親河,可他很少提及,這大概是因為他逆著木蘭溪的方向到達了京城開封,最終成為曾經左右過朝政的人物。南望木蘭溪,它小得就像滄海一粟,蔡襄只能用「海隅隴畝之人」來形容自己。

木蘭溪盛產一種麻石,遠看灰暗樸素,近觀晶瑩剔透。在水流長年累月地沖刷下,麻石變得圓融,小如雞子,大如荒山。在一些奇石愛好者看來,這種麻石無足可取。可只有當地人知道,它們是建築材料中的棟樑之材,不管風吹日曬,萬年不腐。
沒什麼東西比木蘭溪的麻石更容易讓我聯想到蔡襄,他明明可以憑借詩文一驚四座,卻竭力摒棄浮誇文風。他拒絕做一名炫耀文采的詞客,也無意於成為一名個性張揚的書法家。他勵志做一名精通政務的士大夫,以實現儒家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宏遠理想。他有自己的原則和操守,卻又深諳妥協與進退之道,為人處世,來去皆從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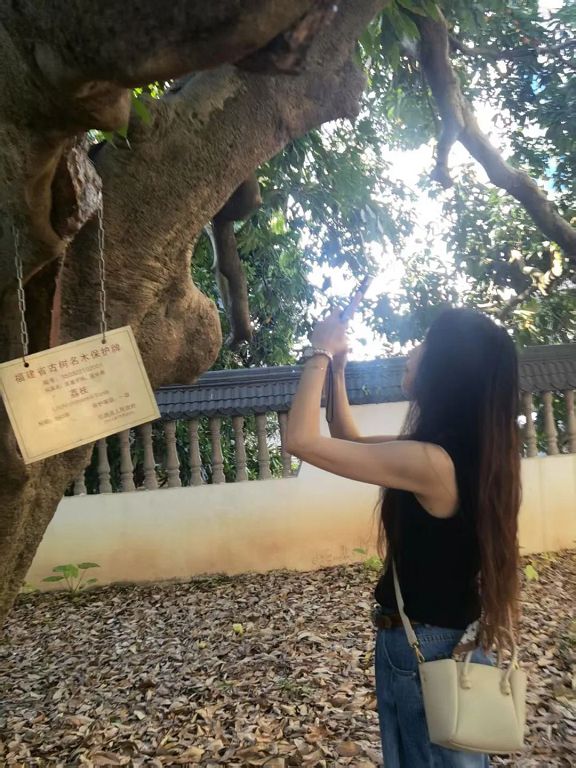
木蘭溪的兩岸種滿了荔枝樹,古歷六月中下旬正是成熟季節,火紅的果實沉甸甸掛在枝頭,那是大地賜予這方子民的財富。我因為參加「莆陽御史文化的歷史鏡鑒與當代價值——以蔡襄等御史群體為例」新聞沙龍活動,有幸第一回見到了荔枝樹。從小就見慣荔枝幹的我向當地朋友問道:「你們是如何做荔枝幹的?」他們利索地反問:「為什麼要做成荔枝幹,吃鮮的不好嗎?」朋友的話讓我切身體會到蔡襄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宣傳家鄉的荔枝。


荔枝的價值,對於普通人來講,不過是滿足口腹之慾,但對於也是北宋理財家的蔡襄來講,那是放眼全國最有特色的地方風物之一。可惜因為它的保鮮期太短,無法像茶葉一樣擠入硬通貨的行列。蔡襄心有不甘,如此天然美物,值得向世人宣傳,所以他固執地給幾千里外的師友們寄送新鮮荔枝,哪怕壞了也無悔。為了讓世人看到新鮮荔枝的生動模樣,他還請專業畫師畫荔枝,宋代士大夫格物致知的精神在他這裡發揮到了淋漓盡致。最後,他還深入民間進行考察,用擅長的小楷精心撰寫了《荔枝譜》,再刻石拓片,無限複製,永久流芳。

蔡襄離世已經快一千年了,木蘭溪的水仍然川流不息。他誕生在仙遊楓亭楓慈溪畔,後居住在木蘭溪邊的蔡垞,作為莆陽大地的孩子,蔡襄似乎從來未曾離去過。他老家村頭那棵荔枝樹已是參天大樹,年年著花,歲歲結子,毫無衰敗之跡。如今,一座規模宏大的「莆陽御史文化館」矗立在木蘭溪畔。當地融合莆田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悠長文脈,探尋傳承千年廉脈,挖掘呈現了246名莆陽御史生平事跡,在這裡集體亮相、展示,堪稱創舉。而現在也只有300來萬人口的莆田,史上如此御史輩出,讓人驚歎。在館內,著名諫官蔡襄的故事領銜演繹,格外引人矚目。他那被「書法家」的標籤所掩蓋的優秀士大夫品質,正為更多世人所知曉。在莆田,我還聽到方言俗語「清跟木蘭溪水一樣」「清明如蘭水」,我想,那也是木蘭溪母親河給予蔡襄最好的歸宿。

仇春霞,中央電視台《百家講壇》《百家說故事》欄目主講人,影響廣泛的非虛構歷史專著《千面宋人》作者。現為北京畫院理論部研究員,中國工筆畫學會理事。編有《書論備要》《畫論備要》等學術著作。
作為古典文學碩士、美術學博士,她長期致力於宋史研究,撰寫《千面宋人》獲文津圖書獎提名。書中收錄宋代60餘位名士的120餘幅書信,其中對北宋莆田籍名臣、著名諫官蔡襄有眾多獨到解讀詮釋。在《百家講壇》等欄目,她主講了45集關於宋代人物故事 。



介紹皮影製作過程。-768x512.jpeg)
